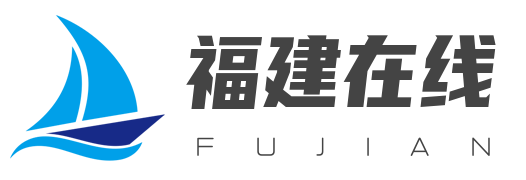《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阅读体验就像被人猛地推进一个线索混乱的揭秘游戏。在品读的过程中,读者的胃口是被作者吊着的:叙事的非常规、复杂化——不同的叙事角度、颠倒交错的叙事时间与丰富的叙事空间,搭建了作品的迷宫结构,在每个章节让都读者产生不同的疑惑(爱米丽为何如此神秘?贵族的房屋为何散发臭味?毒药是为谁准备的?爱米丽的爱人为何凭空消失?)。陌生化的写作手法为读者设置了“阅读障碍”,不似阅读单向线性叙事时间作品那般被情节推着往下走,而是充分调动读者的“侦探意识”,将一个个线索串联,最终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阅读快感。而且有意思的是,对于不同阅读能力的读者而言,所收获的阅读快感是同中有异的。
对于这部短篇小说,才疏学浅的我读了两遍才大致梳理明白故事:可怜的贵族女人“爱米丽”去世了,一个一生都被父亲的阴影笼罩下的南方“淑女”,守着她对旧体制的坚持和对幸福的渴望在一座破败的别墅里孤傲地生活了四十余年。读后的感受就如福克纳的行文线索一般有些迷糊,但我明确且急切地想找寻一个问题的答案—— 送给爱米丽的“玫瑰”除了是幸福的象征外,还能是什么呢?这些“玫瑰”藏匿在哪儿呢?
“玫瑰”这一意象,中外作品中常出现,且象征意义非常丰富:对热爱事物的坚定追求、对女性的同情或赞美、对美好事物的感叹等。斟酌思考后,我认为“玫瑰”在此部小说中,不仅是幸福和爱的象征,也包含着着一种无奈和感慨。
(一) 对南方传统贵族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祭奠
作者或者说镇上的人们对爱米丽的的感情是复杂的,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态度。
面对这个贵族代表者,第一代人尊重且维护着这个白人贵族的象征,就如小说的开头所言,男人们因“爱慕之情”来送丧,将爱米丽的死亡称作是“纪念碑的倒下”,且将她的墓地被安排在了南北战争的军人墓中。美国南北内战的结束,工业机器战胜了农耕庄园,南方贵族的“伊甸园”被毁灭。而在汽车和轧棉机之类物品堆积的曾经最考究的街道上,有这一座“桀骜不驯”的古宅,住着一个象征传统的爱米丽。她是镇上人们怀念回望曾经的“时光镜”。她似乎有着能同所有新事物抵抗的能力:一生不曾纳税、拒绝挂门牌和设邮箱,她用那封锁四十年不止的前门,傲然得坚持着她作为南方传统贵族的尊严。而镇上的人们(多数是第一代人)也有着对爱米丽的一份“心意”:镇长用无人会信的理由给了爱米丽税务特赦,年过八十的法官会用“怎么能在贵妇人的面前说”这样的话语阻止人们对爱米丽进行正面的争执,大家也会将孩子如同星期日去礼拜一般虔诚地送去爱米丽那儿学画......最为诚恳的是,在文中有两处将爱米丽与“偶像”并提。在美国南方,一个父权制度长期笼罩下的小镇,将一个落魄的贵族女子称为“偶像”,不是因为她所具有的人格魅力,而是她南方“淑女”身份下所象征的传统贵族,是人们对南方旧有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和社会传统的维护、对逝去历史的一种缅怀。
随着工业文明的在南方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经济结构带来新思想,新一代开始冲击旧有的传统贵族价值体系,传统贵族势力逐渐式微。“破败的房屋“、“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不鲜艳的墨水“、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失去光泽的镶金”等细节都在暗示着我们:曾经的贵族荣光已不在,北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资本终将击溃南方庄园经济滋养出的传统贵族。“一年又一年纳税通知单”、“无人去上的绘画课”、“对爱米丽的一无所知”,镇上的一代又一代也不再对这位传统贵族象征有多余的感情,不给予过多的关注。直至爱米丽的秘密被“我们”撬开,那个用玫瑰色填充的装满爱米丽对幸福的渴望的屋子被发现时,“玫瑰凋零“,南方传统贵族的最后一丝尊严被剥落,用最不体面的方式完成谢幕,而后走下历史舞台。
(二) 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的无奈
在这篇小说里,爱米丽的男仆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勤勤恳恳地为这个没落的白人贵族工作了数十年,但他的名字只在爱米丽的口中里出现过一次。余下的出场里,一个普通且随意“黑人”就是他的身份指代,在年过八十的老法官的口中更称其为“黑鬼”。爱米丽活着时,就算大家对爱米丽有着好奇,也没有人想要同他有过多的接触;爱米丽死后,他的不知所踪也没人在意,谁也不会去讨论他的何去何从。除了这一重要角色的描述,文中也出现了几处对黑人处境的描写,对“沙多里斯上校”的解释是“下了一道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命令”,那个不知作何用途的毒药是由一名黑人送货员交给爱米丽。
在这部小说里,读者也能隐隐地感受出来黑人所处的尴尬地位。南北战争消除了南方的奴隶制,为黑人争取了人权自由。但实际上,种族歧视一直都在美国社会中存在,黑人歧视未曾消失。直至今日,仍有不少种族歧视问题亟待解决。
(三)父权社会束缚下的女性悲剧的感慨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格面具”。生活在南方传统白人贵族家庭里的爱米丽,母亲早逝,被父亲严格控制下的她,带着最为标准的南方“淑女”的面具:成为父亲支配着的“提线木偶”。因此当三十年来所依靠的父亲去世时,她的绝望与无助是多么的具象化:一连三天都否认父亲的去世,拒绝对父亲的尸体进行埋葬,直至自己死亡,父亲的炭笔画像都悬挂在墙上......
在传统和变革夹击下的爱米丽,也曾有过反抗,也曾尝试放下这困住她三十年的“人格面具”。她将自己的头发剪短,爱上了一个北方男人,不顾镇上人指指点点,和爱的人驾着轻便马车自由潇洒地在镇上,不去在意所谓的“贵人举止”、“阶级对立”。但她失败了,因为放浪不羁的恋人和她从始至终所接受的“父亲的影响”。母亲的早逝、家族其他分支不密切,加之父亲的严格管理,让她的人格另一半“阿尼姆斯“牢牢地烙印下父亲的影子——偏执和极强的控制欲。当爱米丽所追求的幸福幻灭时,“阿尼姆斯“促使她显现“本我”的欲望:杀死情人,并将尸体藏匿在她为自己搭建的“幸福屋”里近四十年,她也重新带上了南方传统贵族的“面具”,成为旧体系的护卫者,将自己隔绝在古宅里。
除了爱米丽以外,还有两个贵族女人——爱米丽的两位堂姐妹。在“我们”得知爱米丽要和北方佬结婚的消息时,我们高兴的却是“两位堂姐妹比起爱米丽小姐来,更有格里尔生家族的风度”。“格里尔家族的风度”大抵是南方传统贵族体制下南方“淑女”的模样吧,在种植园经济下,女性在父权制度的笼罩在成为顺从柔弱、风度优雅的附属品。爱米丽的“结婚喜讯”和“我们”的高兴原因形成的对比,带来了戏剧的讽刺效果:父权社会价值体系下对女性价值的贬低。
如果说父亲和同他一般逝去的南方庄园贵族体制是诱导爱米丽搭建自困牢笼的引子,那么父权体制阴影下的镇上人们的指指点点、自以为是和无情观望则成为加固爱米丽牢笼的钢架。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一题目为小说增大了思索和想象的空间,而“玫瑰“这一意象对表达小说的主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宁夏大学
管韵怡